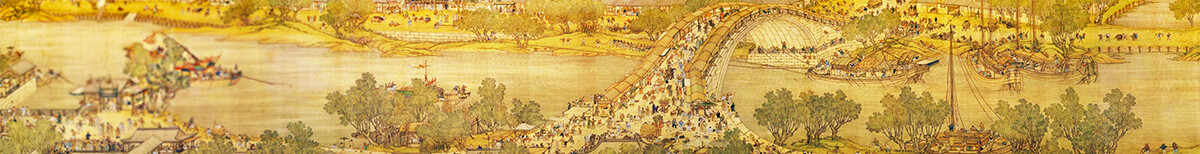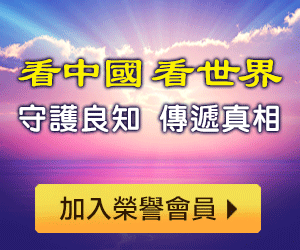六四影片(图片来源:网络图片/视频截图)
【看中国2024年6月6日讯】2023年3月,一个冰冷的雨天。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,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。此前,有人在网上找到他,说自己有一些“六四”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。
匆匆一面,暮色中,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。寒暄几句,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,说:“我保存了这么多年,今天就交给你了。”两人握手告别,他未及细看东西,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,已是深夜。
待他打开袋子,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。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,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“西北大学”。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,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,已接近墨色。
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。隔了34年,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,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。捐赠者告诉他,1989年6月3日深夜,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,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,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,鲜血涌出。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,情急中扯过旗子来,为这个男生包扎。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,浸透了血渍,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。
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。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,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,看起来朴素平淡。一层被他出租出去,租金补贴日常。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“六四”文物的地方。
纽约的“六四纪念馆”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,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。里面的藏品,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,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。2022年初,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,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,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,带走了这顶帐篷,一直保存了下来。

除了旗帜、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,还有一些艺术品,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,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。
其中一张水墨画,创作于1989年6月5日,作者不详。画面中间,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,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。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,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,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,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,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,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,当场死亡。

“六四”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《妈妈你帮我问一问》(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)
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,曾在《历史在鞭打现实》一书中,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:
“车至德胜门,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。一群人,泪流满面,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,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,他那幺小,身上那么多枪眼,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,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,那张小脸,阴惨的白,小脸上的困惑,在我的眼里,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。
人们抬着他,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。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,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。
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,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,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,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。人们先是眼泪,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。我流了泪,却再也愤怒不起来,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,活着意味着什么?
这十五年来,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,一直无法驱散。我总是在想,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,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,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?”
—《历史在鞭打现实》,马少方,2004年
1989我的少年记忆
1989年的春夏之交,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,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,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,十四、五岁的年龄,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,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。
“六四”的爆发,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,不光是我,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。今年5月,发表于自媒体“Women”上的一篇文章《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》,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,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。1989年,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。我们相距上千公里,记忆却如此相似。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,当年的学生运动,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,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。
她在文中写道:“那年发生的一切,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,而是潜入生命底层,指引此后的路途。”我深以为是。我们都在“八九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,大学毕业工作后,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,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。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,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,看到相似的表述,他曾经写道:“1989年6月,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。”

1989年5月18日,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,向天安门广场进发,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。(图片来源:Toshio Sakai)
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都是八九一代——1989年发生的事情,在某种意义上,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,又目睹了“六四”屠杀之后不久,邓小平1992年“南巡”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“向钱看”,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,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。
而那个夏天,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,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。五月的一天,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,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,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。我至今清晰记得,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:“打倒腐败,惩治官倒,声援静坐学生。”
我所在的县一中,坐落在一道山梁下,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。“六四”过后的一个深夜,四层的教学楼上,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。第二天课间,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,让赶紧撤掉。没有人动,我们冷眼旁观。
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,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,平时备受师生尊重。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,我后来关注“星火”案,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。如今想来,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,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,他要阻止事态发展,保护他自己,也保护老师和学生。
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,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。一天,受全班同学的委托,我去了镇上的邮局,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.5元人民币的班费。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,我写下地址:“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(收)”。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,非常顺利——没有任何人说,这个地址不够清楚,没法寄到。那一天,我们,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,都深信不疑: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,一定能收到这笔钱。
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、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。
一切开始转向,“六四”突然发生了。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。“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。”单调高亢的声音,一遍遍重复,几乎有一个月时间,天天如此。
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,打算要做点什么。一天,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,每人一朵,从学校走到家里。但最终,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,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。再后来,掩盖“六四”曾经发生的事实,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。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,余烬也要被清理,“六四”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。
后来我听到一句话:“谎言重复了1000遍,也就成了真理。”事实上,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,并没有成为所谓“真理”。34年过去了,2023年的6月4日傍晚,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“六四”纪念集会上,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。他说,至少,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。

2023年的6月4日傍晚,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“六四”纪念集会。(图片来源:Leonard Munoz)
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,名叫董泽华。当他通过“翻墙”知道了“六四”的真相,就再也不能忘怀。2019年“六四”三十周年时,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,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,结果被抓并判刑。同一天,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,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——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。
如今,35年过去了,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,要让人们忘记“六四”的存在,忘记屠杀,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。但事实上,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,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,始终都在那里。35年,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,但关于“六四”的记忆并未曾断绝。
本文涉及的人物:
林培瑞:
出生于1944年,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。
周锋锁:
出生于1967年,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。
作者江雪:
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,1989年时是中学生,后来一直做记者、编辑。
邹幸彤:
出生于1985年。香港大律师,前支联会副主席,因坚持纪念“六四”及相关工作,如今在狱中。
晓明:
出生于1989年,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“六四”胎教。
董泽华:
出生于1991年,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“六四”三十周年而被判刑。
曾雨璇:
出生于2000年,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,2023年“六四”前因计划展示”国殇之柱”横幅,被判监禁6个月,后遣送回大陆,失联至今。
纽约“六四”纪念馆:“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,不再怕被驱赶”
五月的一个下午,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,人流如潮水。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,门牌号“894”,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。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,上电梯,“六四纪念馆”就在四楼。
六四纪念馆决定从7月19日起,增加每周三下午12时至4时对公众开放。原有的每周日下午12时至4时的开放时间继续保留。和此前一样,每一个成年参观者均需在一份参观规则上签字表示同意。请您在来访之前,阅读“开馆公告”以获知注意事项:https://t.co/AxeD50cqrx。我们期待您的光临。 pic.twitter.com/BrspAGXI8N
— 六四纪念馆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(@64museum) July 16, 2023
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,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(纽约宾州车站)出来,七八分钟时间,便穿街走巷到了“六四纪念馆”楼下。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,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,已十分习惯。
能在纽约的“心脏”部位找到一处“六四纪念馆”的地址,于他已十分快意。何况第六大道这个“894”的门牌号,简直如同天赐。新冠疫情中,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,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,这也给了他们机会。最终,2022年2月,“六四纪念馆筹委会”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,租下了这个地方,面积大约2200平尺(约合204平米)。
此刻,站在玻璃窗前,脚下纽约人潮如海,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,而“六四”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。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。“今年是历史的一刻。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。不像过去,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。”
和其他“民运人士”惯用昂扬词语不同,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。“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。”他说,这是一个事实,过去很多年,“民运”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,很多活动,参与者寥寥,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。“那怎么办?还得坚持。”他说。
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,他坐牢,流亡,1996年到美国,先为生计匆忙。后来,创办“人道中国”,关注国内的政治犯,“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”。近年来又接手了“中国人权”的工作。四处奔走之时,“失败感”常袭上心头。2008年,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,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,差点受重伤。还有一次做活动,地方都租好了,又遭人上门驱赶。
这次“六四纪念馆”在纽约找地方,一开始,在几个街区之外,找到一处,房东是台湾人,本来已谈好了,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“六四”有关,就“不敢租了”。如今这个地方,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“六四纪念馆”的标识,以被更多人看到。但谈判了好几次,还是被拒了。
但他一直有耐心,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。他回忆说,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“六四”,也很紧张,慢慢的,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,很真实,清晰,有一种释放的感觉,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。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。“圣经里,摩西说:我口舌笨拙。上帝告诉他,当你开口讲话,我会告诉你做什么。”
“当年,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,现在都在我心里,就想着把它讲出来。”他说,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“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,是很痛苦的,但也有新生的感觉。”
1989年,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,至今,他还这样说:“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,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,有无比的吸引力。”他认为,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。
“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。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。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,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、尊严。”
“无论如何,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。”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。当年“六四”发生的时候,他在美国求学,“六四”的爆发影响了一生。如今,他认为,只要纪念馆在这里,“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”。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,设计展板,安放每件文物,修空调,种种琐碎之事,都要自己一一去做。
时光无情,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。2021年,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“六四纪念馆”被迫关闭,港大校园里的“六四”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。有更多与“六四”有关的人与事,正在凋零。从这个意义上,“六四纪念馆”也是和时间的赛跑。那些历史的见证物,如果无处安放,终究也会流失。纽约的“六四纪念馆”筹建后,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“六四”的东西,包括当年的报纸。如今,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。
玻璃墙上挂着的“六四纪念馆”几个字,是鲍彤2021年写的,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,2022年11月去世。
纪念馆入口处,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,估计有50公斤重。推印的那一面,蓝墨色还在。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,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,他形容自己的心情,“犹如故友重逢。充满喜悦,又难以置信。”
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。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,“新闻自由”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,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“新闻自由”的传单,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,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。题目就是“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?”

1989年5月22日,官方报纸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举着“取消军管,保卫首都”的横幅,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,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。(图片来源:Catherine Henriette)
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,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,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。1989年5月,在天安门广场,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。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,有一个“高速油印机”,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,工作效率非常高。
“六四”凌晨,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,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,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。当时那么危急,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,说:“这是好机器。抬回去继续战斗!”“是的,继续战斗!”那时候他也这样想。
33年后,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,翻来覆去,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,“孔雀21型速印机湖北江汉工业公司87年7月机号0159”。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“速印机”,与记忆完全吻合了。
油印机的捐赠者,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。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,后来母亲去世,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,继续保存。2022年,姐姐费尽周折,把它带到美国。出关时,为了安全,拆掉了所有标志,只说是“工业样品”,还好,没有遇到太大麻烦。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一路紧张,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。
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,也是历史的证词:
“六四凌晨五点左右,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,正在争论的时候,子弹从头上飞过,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。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,从上往下驱逐学生。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。
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,我们抬到广场边上。一个同伴,也是清华教师,有自行车,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。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。期间,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。当时,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。
坦克开过来的时候,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。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。我直勾勾看着坦克。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,停下来掉了头,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。不是杀伤性的,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……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。
在同一地点,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,窒息死亡。”
纪念馆的玻璃墙上,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,那是年轻的《解放军日报》记者江林的,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,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。
还有一个红袖带,是当年“清华纠察指挥队”的,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。还有一封信,内容是一个军人,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。
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,发生了很多故事。周锋锁说,一次,听到“六四纪念馆”在筹建的消息,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,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“六四”期间的日记。今年5月22日,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,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“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”的传单,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,但看得出时间,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。
两天后,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,和另外几件“六四”文物一起,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。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,也邀请他去交流,并做展览。年轻人的热忱,让他深深感动。

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。(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)

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。(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)
35年了,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,在全世界。
“就像这个油印机,其实一直在等待着,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。”周锋锁说,他觉得,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,是带有使命感的。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,受伤的人,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,保存下来。
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“六四”?
2023年3月,我漂泊到纽约。作为一个记者,第一次,因为离开了中国,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“六四”,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。
6月4日这天,“六四纪念馆”正式开放。这一天,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。开幕仪式上,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:“为什么要记得六四?”
此前,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,是用中文读诵的。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,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。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,积极的“六四”参与者,曾在中国被劳教,饱受屈辱,1997年到达美国。
“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?”
“我们记住六四,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。今天,他仍然是17岁。他永远是17岁。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。”
“我们记住六四,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,始终困扰着刘晓波,直到他去世;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,直到我们也去世。”
“我们记住六四,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。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,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从来也不知道。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,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……”
“我们记住六四,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,但也是最好的中国。”
“我们记住六四,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,自己有什么记忆……”
那一刻,小小的纪念馆里,挤满了人,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,声音哽咽,红了眼眶。1989年6月4日那天,他就在北京,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,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。
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,我在玻璃门外,一瞬间泪如雨下。也是在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,30多年过去了,作为一个中国人,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,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,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“六四”,也让眼泪肆意流淌。
1989年以后,“六四”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,每年“六四”前后,政府都如临大敌,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“自我审查”,不敢有任何关于“六四”的信息成为“漏网之鱼”。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,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,或者一朵白花,你就知道,有一些人,还记得“六四”。但近些年,就连烛光或花,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。
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,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,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,没有忧惧地纪念“六四”。
2014年5月,浦志强、徐友渔、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,在北京的家中纪念“六四”,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,多人被抓捕。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,他因此被判刑入狱。
我的一位朋友,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。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“六四”。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,他在微博上发了条“今日无话可说,休息”。几分钟后,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。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,闻讯赶到现场,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。最终,警察没有带走他。但几年后,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,而被判刑4年,至今还在狱中服刑。
我记得,1992年,“六四”的肃杀尚未过去,我到西安上大学。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: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,原本是学校的老师,因为当年参加了“六四”,不能再当老师。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,也是同样的遭遇……
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,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,因参与“六四”,以及在“六四”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,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,出狱后,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,直到2020年去世……事实上,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,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,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“六四”而付出他们的代价。
也可以说,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,“六四”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。
“六四纪念馆”里,挂着一副书法“爱国无罪”,写字的人是宁先华。这个壮实的男子,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。他在“六四”后一度失去自由,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“民主党”的工作,2007年,再次被判刑12年。后经减刑,于2016年出狱。2017年,他辗转离开中国,如今,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。纪念馆开幕的这天,他是现场的义工。
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以及“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”
“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?”
2023年春天,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,我问晓明。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(后改为“热风”)的发起人。2023年3月25日,沙龙的第一场活动,就是在“六四纪念馆”举办的。
1989年的秋天,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,他还在母亲肚子里。母亲那年25岁,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,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,下班要走很远的路,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。母亲喜欢看热闹,说她一边走,一边听学生演讲,也不觉得累。她也听美国之音。晓明笑着说,这都是他的“胎教”。
但他第一次知道“八九六四”,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。那天,体育老师来代课,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,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。他回去问了家里人,小姨才告诉他,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,去世了,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,“搞了这个活动”。
只言片语,却唤起了他的好奇。2008年,他上了大学,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“八九”。再后来,他读《城市画报》,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,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,“八九”是一个转折点。“八九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,“八九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。他对此感到不确定,不知道“八九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,“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”。
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,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。但在“墙内”,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,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。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《河殇》,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《河殇》的书,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,始终看不到《河殇》的片子。
有一段时间,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,印象深刻。他记得,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“六四”,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:开枪之后,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,吴低沉地说了一句:“共产党完了”。
这些都是蛛丝马迹。可“六四”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?他满怀着好奇。一直到2012年8月,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,没有了防火墙,才终于有了机会。
“我一下飞机,就打开YouTube,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,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。后来,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《天安门》纪录片。”晓明回忆。
他说,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,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,应该“见好就收”。一直到2022年,一个年轻人的媒体“文宣中国(公民日报)”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“六四”历史,包括清场记录,每天有一个大事记。“我通过这个大事记,才了解到,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,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。我也慢慢认识到,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,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,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,说撤就撤。”
2015年左右,出国两年后,晓明遇到了第一个“六四”亲历者。那是他的一位同事,1991年毕业于北大。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,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。
晓明记得,也是在这一年前后,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《天安门对峙》一书的作者,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。“当时,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。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。”他回忆。
2023年底,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。此时,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,通过片子,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。“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,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。”
他记得,在纽约,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,提出的诉求里就有“反对警察暴力,保障人民权利”。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,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,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,保障人民权利。
白纸抗议发生后,纽约的一些活动,晓明也参与其中。他发现,关于“六四”的记忆还是断代的。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,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,举着赵紫阳的像,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。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,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,以及其他的抗争者。
2022年11月,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,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,那之后,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。当时,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,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。
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。早先年,他读钱理群关于“民间思想村落”的文章,知道了在文革后期,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,大家彼此分享思想,他觉得很受吸引。最终,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。沙龙第一期,就邀请了胡平等人,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。
议题的选择,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。
当时“六四纪念馆”已经租下来了,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。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,但还是吸引了二、三十人参加。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,一位女士的提问,是关于“白纸抗议”中的年轻人。而这位女士,正是“六四”的见证者、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。
沙龙开始,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,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,这是新鲜的事情。晓明解释,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,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“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”,于是,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。每次活动,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。“这是在美国。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。”
“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?他们没有说。我也不管。我想,您到我(沙龙)这里来,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。”他说。
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。晓明说,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,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,但他认为,不同世代之间,虽然观点不同,还是可以对话的。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,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。
他记得一件事情,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,现场有人提议,“我们唱国歌吧”。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: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,香港人,大家各有创痛,所以不唱国歌,可以唱国际歌。“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,质问我,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?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!你是谁?我解释了半天,对方也听不进去。”
晓明说,还有一次活动,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,对方也是很警惕。一直追问他“你是什么组织的?”他说,我没组织,我是某某某,并做了解释。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。
“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。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。其实今天我们觉得,最重要的,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。”晓明说。另外,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。
“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,我不喜欢。因为这样的词,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、保守,政治光谱还是不同……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。我特别害怕大词。说一些大词,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”他认为,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,但人在美国,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,话语上和传统的“民运”其实有很大不同。
说起周锋锁,他觉得,“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,他一直很愿意帮忙。”
2023年“六四”,因“六四纪念馆”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,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,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。6月11日,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,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。2023年11月,民主沙龙改名为“热风”,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。
“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,而我,不是这样。除了民主自由之外,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,那就是包容多元。我做热风,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。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,也不想被贴上‘白纸一代’的标签。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,并能参与其中。”2024年5月,晓明这样说。
“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,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⋯⋯无论如何,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。”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,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。
行动的价值:“极权下的反抗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”
“很多人纪念六四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,会到天安门广场去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?而且你那么年轻,六四发生时,你还没有出生……”
2023年6月4日,哥伦比亚大学的“六四”纪念集会间隙,我问董泽华。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,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。
“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……”他笑起来。
1991年,董泽华出生于西安。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,家境算是“小康”,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。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。“我喜欢留长头发,但从小到高中,都被老师揪出去,强迫剪头发。和监狱里一样。”在他的记忆中,学校的应试教育,从小长大的经历,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,遭遇诈骗,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,都让他开始思考,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。
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,“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”,但没有说是什么。一直到上了大学,他学会了翻墙,看到了外网的消息,才知道“六四”死了那么多人。“看了后,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”。
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。“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,明白了,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,是它不诚实,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。例如大跃进、文革,每件事都在撒谎。你会看到,社会底层一些的人,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。”
他告诉我,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:你出生在1991年,和1989年没关系,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?但第一个问他的人,还是北京的警察。
而他告诉警察的,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:因为他做了一个梦。
他告诉我,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,而是真实的。2019年,是“六四”30周年,算是大日子,从五月份开始,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,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,BBC记者曝出了关于“六四”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。
他说,也许是“日有所思,也有所梦”。五月底的一天,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、白衣服的女孩,哭着对他说: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?
他说,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。但他因此决定,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。
2019年6月4日中午,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,并发了一条推特。随后,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。但是,“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,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。”
他穿着“纪念六四三十周年”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,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,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。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,看到另外一个男生,也穿黑衣,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,有江泽民的头像,被他认出来了,就打了招呼。后来,他们成了法庭上的“同案”。
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,听他们对“六四”的看法时,警察来了。最终,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,被以寻衅滋事罪名,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。
2020年1月3日,董泽华出狱,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。2022年10月,他离开了中国。在纽约,他和另一名自己的“同案”重逢。此后不久,“白纸抗议”在国内爆发,在纽约声援“白纸行动”的万圣节游行中,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、很多次在“六四”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。
如今的董泽华,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,但没有停止思考。他说,其实白纸的抗争者,和八九一代一样,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。“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。他说,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。“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,太不容易了。

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“天安门自由女神”像。(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)
2024年的这个春天,“六四”35周年在即,周锋锁奔走四方,脚步匆匆。他去了欧洲、加拿大等多个地方,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《幸彤在监狱》的放映。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,2021年6月,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,被香港警方拘捕,至今还在狱中。
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。曾雨璇今年24岁,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。2023年六四前,她和周锋锁联系,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“六四国殇纪念柱”的直幡。后被指控煽动罪,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,刑满后,被遣送回大陆,从此失联至今。
5月28日,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,在学生举办的“六四”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,除了刘晓波的头像,也摆放着邹幸彤、曾雨璇的照片。在开场白中,周锋锁说,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。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。
也是在同一天,在香港,警方首次以违反“基本法”的23条为理由,抓捕了6个人,称他们利用“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,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”,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。
这个所谓的“敏感日子”,正是“六四”。
“在香港,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。”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。在法庭上,她也曾这样表达:“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,生而为人,我们只有不服从。”
无论如何艰难,35年之后的今天,关于“六四”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。“极权之下的抗争,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。”周锋锁如是说。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。
(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)来源:歪脑
短网址: 版权所有,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。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.
【诚征荣誉会员】溪流能够汇成大海,小善可以成就大爱。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: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,成为《看中国》网站的荣誉会员,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,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,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,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。